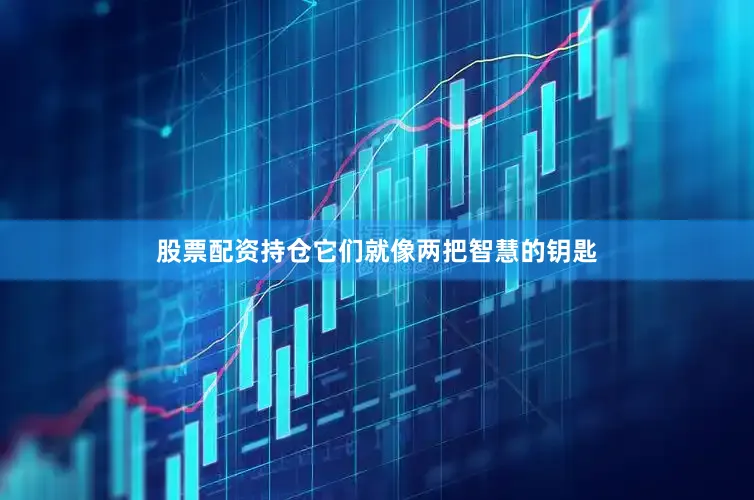来源:8月29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作者: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
这是一场持续8年的行走,和十条穿越硝烟的迁徙之路。
2017年春,四川作家聂作平踏上了寻访抗战中大学内迁之路的旅途。
此后8年,从浙江大学办学的湄潭文庙到华中大学租用的喜洲古寺,从西北联合大学翻越秦岭的旧道到复旦大学落脚的北碚村庄……他循着十所大学的内迁轨迹,重访传奇发生地,尝试以更贴近、更具体而微的当代视角,还原抗战中弦歌不辍的壮举。
近日,记录这段足迹与感悟的新书《山河万里: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》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。
此前,对这段历史的寻访和书写多限于单所院校的线路,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西南联大往事。像这样横跨十校的实地踏访,是第一次。
展开剩余94%聂作平近照。(受访者供图)
寻访的理由
出发的理由很简单:一摞老照片,一部旧日记。
2016年夏,聂作平为给央视一部关于竺可桢的纪录片撰稿,赴京拜访了年近九旬的竺可桢之子竺安。
在竺安家中,他见到几本由竺可桢拍摄的老照片,其中许多都摄于抗战年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:浙江建德,江西泰和,广西宜山,贵州湄潭……
“这些珍贵的照片让我很受触动。”他后来回忆,和许多人一样,他早听说过这段历史,却并不清楚具体细节。
当浙大西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、时任校长竺可桢亲手定格的西迁往事透过黑白影像撞入眼帘,那些史料里“文军长征”的记载,骤然变得清晰而鲜活。
1931年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东北大学遭日军侵占,成为首所内迁的中国高校。此后十余年,日军对我国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实施了大规模的蓄意摧残。为赓续文化命脉,留存民族复兴的火种,百余所大学相继向后方转移,在世界历史上掀起一场举世罕见的高校大迁徙。
浙大西迁,是这场迁徙中动人的一笔。
那次拜访后,聂作平埋首翻阅几百万字的竺可桢日记,发现浙大从1937年被迫西迁到1946年重返杭州,流亡办学近十载,竺可桢几乎记下了每一天的天气物候、工作事务、人际往来、旅途行迹……有如一部微缩史书。
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日益强烈: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,重走浙大西迁路。
他想探访关键地点,去找找竺可桢镜头下建德的牌坊、宜山的校舍,师生们在湄潭上课的庙宇和做科研的茶场……站上当年的坐标,亲眼看看史料文献里的地方如今什么模样,再以文字重现和致敬这段历史。
2017年3月,聂作平从成都自驾前往湄潭。冒着春雨,踏入浙大曾经的校本部湄潭文庙时,他尚未料到,这趟为一篇文章开启的旅程,将在之后数年生长为对更多大学内迁之路的追寻。
位于湄潭永兴镇的浙大教授宿舍旧址。(受访者供图)
同年秋,重走浙大西迁路的文章发表于《南方周末》,读者回应如潮:有人感慨“越是艰苦的时刻,人的斗志也是最强的”,有人追问“苦难铸就的灵魂和精神现在还在吗?”,有人自省“自己丢了很多东西”,有人表白“我是大学生,我想把这种精神再找回来,带回来”……
这些滚烫的回响,推动聂作平继续上路。毕竟,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从来不只是某一所学校的传奇,而是山河破碎之际,中国高等教育的集体突围,成就了烽火中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观,尽最大可能保存了文化火种。其间的艰难悲壮与慷慨激昂,动人心魂,荡气回肠。
只是今天,提起这段过往,人们最熟悉的唯有西南联大。
图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(资料照片)。新华社发
“我想写一些同样影响深远,但人们了解不多的大学西迁故事。”聂作平生出一个愿望,“这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。在国家空前的危机下,那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精神,那些大学在困境中的浴火重生,应该永远被记住。”
武汉大学、华中大学(今华中师范大学)、东北大学、西北联大、厦门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中央大学的内迁之路,先后出现在他的足下与笔下。
出发,归来;再出发,再归来……他踩着内迁师生的足迹,一次次往返奔波于广袤大地,试图以行走与书写,让被时光模糊的历史重新被看见。
大地上的细节
万事万物在时间中沉淀而有历史,在空间上存在而有地理。探访历史现场,以承载记忆的地理空间作为解读历史的钥匙,是聂作平近十年来写作的特质,也是他的乐趣所在。
用聂作平自己的话说,旅行是他的工作方式,他的大半作品“既是用手写的,也是用脚写的;一半在田野上走完,一半在书斋里写成”。
这种“手脚并用”的寻访式写作,如何进行?
首先,是大量文献阅读与资料收集。为写抗战大学内迁往事,聂作平读了数百本校史、回忆录、方志、政协文史资料,还读了不少学术论文和专著。
旅途中,他通过方志办等渠道搜集到少量未对外刊印的材料,又从旧书网站淘回一批历史文献,包括大学毕业生名录。借助资料,他梳理出每所大学内迁中的重要地点,手绘线路图,注明每个地点上要寻访的具体去处,如校舍旧址、宿舍故居、历史事件发生地、内迁纪念馆……抵达当地后逐一探寻,与文献记录比对印证。
各校旧址星罗棋布,且不少地方交通不便,自驾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。一些地点轻易可至,但另一些却如隐雾中。
例如,浙大在广西宜山(今河池市宜州区)的旧址“标营”,具体位置众说纷纭。聂作平致电宜州区方志办,得到的答案依旧模糊。
他不甘心,一路打听数位老人,终于问到大致方位,沿一条小路驾车深入,直至尽头——眼前出现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,门前的石狮子曾进入竺可桢的镜头,门内杂草丛生的院子里,老树下赫然是竺可桢所立《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》石碑。
“在清代,这里是军营。上世纪60年代成了部队医院。后来,医院搬走,院子从上世纪80年代就荒废了,所以很多当地人也不知道这个地方。”他至今难忘那条通往标营的小路,路两侧立着许多香蕉树与木瓜树,路尽头的往事被裹在南国特有的光影中。
每到一处,聂作平都会拍摄大量照片,对关键地点,还会以360度全景方式录制视频,力求完整呈现“环境关系”。
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。“比如拍标营旧址,我不会只拍大门和石碑,还要记录周边情况。”他解释,“前人写过的地方,我总想去看看现在是什么样。景观的改变、建筑的更替,都是历史变迁的体现。”
“最重要的是细节。”他反复强调,“为什么我要去寻找这些遗迹旧址?因为那里有丰富丰满的细节。史料始终是枯燥呆板的,但历史本身很鲜活,只有到现场观察和感受,才能找到并再现这种鲜活。”
在云南大理喜洲镇,华中大学曾借作校本部的大慈寺,聂作平站在供奉孔子的奇观堂内,注视画像上的孔子,忽然觉得,华大内迁的故事就该从这间当地人称“文庙”、曾被华大改建为图书馆的殿室写起。
喜洲大慈寺内的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。(受访者供图)
“孔子目光忧郁。”旅途归来,他将这句话写在篇首,“目光忧郁的孔子望着庭院。空荡荡的庭院,一树木槿怒放灿烂”。
“这是我的第一印象。”他问:“不到现场,我怎么会知道孔子的目光?又怎么能看到那树木槿花呢?”
华大师生栖身喜洲大慈寺八载,聂作平先后3次踏访。头回去,看到的大慈寺状若废墟,后两次再去,寺院已明显修整过,还专门设立了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。
只是,3次前往,除了工作人员,他始终未遇他人,不禁感慨:在当事人和极少数打捞者之外,尘封的往事或许难免要被淡忘。
也是在喜洲,聂作平遇到一位九旬老者。年少时,老人亲眼看到华大师生在校长韦卓民的带领下西迁至此,至今记得韦校长朴素和善的模样。几十年后,他与几位同乡自发设立了华大遗址纪念场所,以最朴素的方式,纪念这段岁月。
纸面上的历史,藏着太多没被发现的细节与后续,唯有亲临现场才能捕捉;许多更深的触动,也唯有身临其境才能产生。
喜洲海舌半岛,曾是华大生物系师生研究洱海的取水地。80多年后,聂作平望着前来拍照打卡的年轻游客,感到时空在此折叠,眼前的热闹重叠着另一群年轻人的身影——同样风华正茂的他们“跋涉了千山万水来到这里,在同样的苍山之下,洱海之滨,度过了迥然不同的青春岁月”。
对聂作平而言,这样的寻访数不胜数。那些山川与城镇,道路与建筑、路牌与老树;那些味道与声音、邂逅与发现、回忆与遗忘……
车轮滚滚向前,驶过一个个被标出的地点,散落在大地上的细节被一片片拾起,故纸堆里的地名和记载,便也苏醒于脚下真实的路途与眼前真实的山河。
绝境中的日常
广泛寻访,令聂作平得以更清晰地感知各内迁大学间的异同。
最明显的一点,是这些学校风格各异、境遇有别,但都在战火与困厄中表现出同一种不屈的姿态:“一种向死而生的韧性与狠劲。”
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目睹日机轰炸南京的校园,指着炸弹坑说:“寇能覆之,我必能兴之。”此后,中大师生由南京西迁重庆,连农学院用于实验的良种家畜家禽也绝不留给日寇,跋涉千里,一并迁走,创造了大学内迁中“鸡犬不留”的壮举。
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8年,是学校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,却也是发展迅速、硕果连连的时期:搭建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,完成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,诞生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作《张居正大传》,在世界权威期刊《自然》《科学》上发表多篇论文……
武大学生陆秀丽(右)、唐良桐(左)在乘“民贵”轮入川途中。她们面容沉静,实际却是遭逢战乱的学生,为继续求学,不得不和学校一起迁往异乡。(受访者供图)
英国学者李约瑟1943年赴乐山访问后,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提到中国武大,感叹“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”。
这类危急存亡中逆势崛起的例子,在内迁大学里比比皆是:浙大经历炮火洗礼,由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发展为民国四大名校之一;厦大在抗战中成长为“南方之强”;同济大学战前以医科和工科著称,战后迅速发展为具有医、工、理、法、文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……
无论怎样严酷的处境,都无法撼动中国大学向前的脚步。越是困苦,笔耕越是不辍;越是艰辛,书声越是琅琅。
陕西城固的七星寺,是西北联大五校中西北工学院一年级学生的落脚处。校舍逼仄,夜里自修的学生分成前半夜“开早车”、后半夜“开晚车”的两拨。有上下铺室友因自修“班次”错开,整整一年没好好打过照面,直到二年级换校区后才在闲聊中相认。
因为这些奋发苦读的学生,七星寺的灯光烛火经年累月彻夜不熄,成就了“七星灯火”的佳话。
这燃烧的灯火并非孤例:中央大学让“沙坪学灯”成为重庆著名的“陪都八景”之一;辗转迁至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,每日黄昏都有手持油灯的学子排成长队,等候工人灌注灯油,带回宿舍,学到油尽灯灭……
聂作平时常感叹: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大学能在忧患中浴火重生?一路走来,他边寻觅答案,边将历史的印记与当下风景一并收入行囊。
寻访中,另一点令他肃然起敬的,是笔下这群师生战乱中寄身异乡,却始终不改的乐观昂扬。
浙大教授、数学家苏步青在湄潭时生活拮据,上课之余开荒种菜卖菜,自谓“半亩向阳地,全家仰菜根”。
这般困窘时日里,他与钱宝琮等喜爱古体诗的教授同好还发起成立了诗社“湄江吟社”,旨在“公余小集,陶冶性情”“留一段文字因缘,藉为他日雪泥之证”。9位寄居黔北的数学家、文学家、化学家、农学家、教育学家……一年内聚会8次,在农场、茶场、湄江边上创作诗词258首。
在李庄,同济大学土木系学生俞载道与同学组建起男声合唱队,为校园婚礼献唱《婚礼进行曲》。他们还成立篮球队,省吃俭用,到重庆找中央大学、重庆大学等高校比赛。
位于李庄禹王宫的同济校本部旧址。(受访者供图)
“再艰难,也有生的乐趣。”聂作平把这些常被视作历史“边角料”的逸事拢于笔下,让连天烽火中这群读书人的精神轮廓更为凸显。
他们气宇轩昂的风采气度,在他观察各校老照片时一再得到印证:“无论哪所大学的师生,从神情上,你看不出他们正身处乱世,生活极度艰苦。他们脸上没有萎靡之气,反而很从容、有朝气,有种意气风发的向上的气质。这一点,值得我们思考。”
聂作平认为,至关重要的,是这些师生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。厦大学生潘懋元入学后第一次听校长萨本栋讲话,就是斩钉截铁的宣告:“我们中国抗战必成,抗战一定胜利,所以我们现在培养的是战后建设国家的人才。”
“将士以勇于战阵为救国,官吏以忠于服务为救国,学校以瘁于研学为救国。”怀着这一信念,到抗战胜利时,中国大学非但未被战争击垮,还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。
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从战前的108所增至141所,在校生从4万余人增至8万余人。从中走出的万千才俊,投身民族解放与复兴事业,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翘楚,以学识与担当兑现了为救国而读书的誓言。
值得一提的是,书中,聂作平不但刻画了竺可桢、王星拱、韦卓民、萨本栋、臧启芳、罗家伦等率领大学内迁壮大,为此殚精竭虑、厥功至伟的校长群像,也记录了众多普通师生鲜为人知的际遇与日常。
以内迁之路极为波折的同济大学为例,聂作平用纪增觉、徐为康、傅信祁、俞载道、曾昭耆5个助教、学生的经历,串起同济6次迁徙与重返上海的全程。
他不厌其烦地写他们翻过的山、渡过的河,写他们如何骑车、坐船、搭车、步行,写他们的行李内容、住宿饮食、沿途遭遇……他也细致描摹了他们颠沛流离中的牵挂、忧愤、踌躇与坚韧。
“比起大人物,小人物的生活才最具代表性。”他尽力还原“小人物”具体生活的肌理,“只有知道更多生活细节,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段历史。我一再强调细节的重要,因为我相信,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。”
所有雄壮的故事,都由具体的人、具体的地方、具体的生活融汇而成,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坚守的总和。
延续的文脉
为了解聂作平的寻访方式,6月末,记者随他探访了古蜀道上的几处地标,亲眼见到他如何细致地拍摄“环境关系”,一次次指着路边不起眼的石碑、墙上的告示、桥亭上的彩绘,重复那句:“这都是细节。”
在“川陕咽喉”大散关,望着山壁上“铁马秋风”四个红色大字,他谈起巡视过此地的爱国诗人陆游及其名句:“楼船夜雪瓜洲渡,铁马秋风大散关。”
大散关一带,山壁上的“铁马秋风”。本报记者王京雪摄
西北联大和东北大学的师生都曾在西迁中翻越秦岭、途经此处。写他们的内迁之路时,聂作平很自然地提到了陆游。
他喜欢在同一个地方串联古今,写下交错相连的文脉。写厦大在长汀的礼堂“大成殿”,他会提一句这是朱熹、辛弃疾、纪晓岚讲过学的地方;写浙大暂居吉安白鹭洲,他会顺带说吉安是文天祥老家,这位状元郎正是从白鹭洲书院走出来的;东北大学落脚三台,他讲杜甫也曾客居于此,东大借用的部分校舍相传是其草堂旧址,杜甫还在三台写下了那首令东大学子触景生情、心生向往的名作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……
位于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旧址,图为于原址复建的厦门大学正门。(受访者供图)
走在同一条道路上,他看见不同时代行者的背影,也看到作为后来者的自己。一代代人的跋涉,都回应着前人的足音,山河万里,从未沉寂。他感到“吾道不孤”——“向前看,先贤在那里”。
除了寻访大学,近些年,聂作平还同时推进着多个寻访写作项目,包括杜甫、李商隐等古代诗人的人生地理,《寻秦记》等春秋诸国系列。
他总结,这些写作归根结底都是在道路上寻找文脉。以寻访内迁大学来说,“写的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传承”。
有条件时,他会带儿子一同寻访,希望儿子从小记住那些“可风可颂,可叹可泣的先人”。
镇南关是华中大学等学校内迁的经行之地。作者寻访旧址后与儿子在此合影。(受访者供图)
2017年重走浙大西迁路时,儿子刚满5岁,还在上幼儿园大班。在湄潭昔年的茶场、今日的景区,聂作平清楚记得:“那天下着雨,整个景区只有我们一家人。我牵着儿子,沿着观光小火车的铁轨一直走,好像一直走下去,就会遇见当年那些在这里做研究、指导茶农种茶的师生。”
到他写完这本书,儿子已经是初中生了。去年清明,父子俩一起去陕西古路坝寻找西北联大旧址,看到一片断壁残垣,“天也下着雨,我把车停在那里,四周没有人,就听到山谷里杜鹃鸟啼叫的回声”。
聂作平说,在变化不大的旧址,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又快又慢,仿佛先人刚刚离开;而在时过境迁的旧址,“你会感到忧伤,同时引发对当下和人生意义的思考”。
走完、写完十所大学内迁的故事,他感到,过去作为知识了解的历史,由平面变得立体;而这段历史中沉淀的精神,在今天依旧能予人力量。
“还有好多学校可以写,至少可以再写十所。”他决定继续走下去、写下去,让这本书成为一个起点,而非终点。
他清楚自己走不完所有的路,写不完所有大学的故事,但他相信,只要还有人愿意去走、去看、去写、去读,那不辍的弦歌便永不会消散。
6月初,完成书中最后一篇文章——序言时,聂作平这样写道:
“纵然光阴无情,过尽千帆,但终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,融入后来者的灵魂。
“我走了那么远的路,读了那么多的史料,写下那么长的文字,我仅仅想告诉你——
“在我们栖居的这片土地上,曾经生活过这样一群人,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倔强的身影,执着的声音,孤勇的命运。”
追寻无尽,薪火不灭。
监制:姜锦铭 | 责编:吉玲、刘小草、刘梦妮、刘晶瑶 | 校对:张慧
发布于:北京市融丰配资,券商配资,浙江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日照股票配资不过诺丁汉森林仍在继续谈判
- 下一篇:没有了